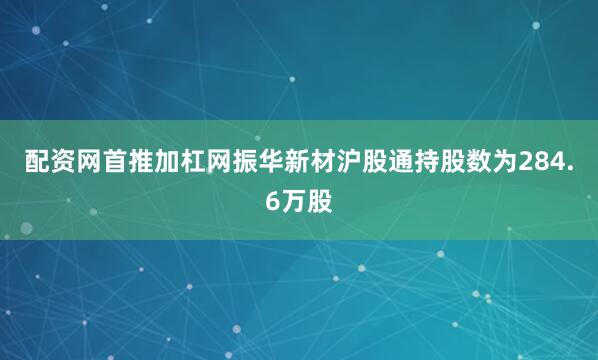在一场访谈中,毛远新深入探讨了毛主席批判孔子的真正动因。然而,这场批孔运动的起源,实则与一首诗作紧密相连——那便是毛主席于1973年致郭沫若的《读封建论·呈郭老》一诗。
少骂秦皇,焚坑事需商。
祖龙已逝,秦朝尚存;十批非佳文。
秦政百代传,孔名虚名高。
熟读封建论,勿效子厚复古。
毛远新表示,这首诗系主席于1973年夏日挥毫之作。然而,他是在“十大”之后才告知于我。而“十大”召开于同年九月。彼时,我正在辽宁履职。会议闭幕之后,我即将返回,与主席作别,此事正是他亲口所告知。
在郭沫若所著的《十批书》中,有一部专论秦始皇,对秦朝焚书坑儒之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。此书于50年代问世,因此,毛主席将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赐予我阅读。我对此文进行了深入的研读。虽然唐朝的古文并不难懂,但当我接触到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时,却感到颇为吃力。许多生僻的字词我都不认识,于是便向毛主席请教。他为我一一解释这些字的含义。谈及明末清初的文章,我感慨它们竟比唐朝的还要晦涩难懂。
主席指出,唐朝时期,文人墨客的作品尚未达到极端,李白的诗作尚能贴近民众心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尤其是南宋时期以后,诸如朱熹的理学等学说兴起,至元明两代,似乎越是用到生僻的字词,人们的自我评价就越高。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中对秦始皇给予了肯定,主席曾以此书与我分享其观点。
一句古语云:秦朝继起,终至覆灭。然而,那倡导“天下为公”理念的秦始皇,其行径亦非全然无私。诚如所言,他虽以一人之私欲成就了公天下,但其内心仍为个人私利所驱使。他所说的“分封制”,正是柳宗元所极力反对的,认为封侯之举只会导致国家分裂,先起纷争,终至历代皆难以避免的各种问题。秦朝统一之后,是否实行分封制,李斯与众多人士意见不合。李斯力主郡县制,主张由皇帝亲自任命省长、县长,而非封王于各地,使子孙世代统治,实现世袭。正是他打破了这一传统,主席赞誉其功绩卓著,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壮举之一。
在秦始皇之前,诸侯王侯林立,而秦始皇继位后,却觉得分封制已不再适用,于是推行了郡县制度。随后,有些朝代又恢复了分封制度,比如汉朝初期,七国之乱、八王之乱接连发生,使得汉武帝不得安宁,众多诸侯纷纷起兵造反。汉朝的分封制度,延续至唐朝,李世民时期仍需封王,对于立有功勋者亦需封赏,然而是否封王在朝内引发了诸多争议,历代皆然。比如,若某一省份需封王,那么王位将世袭,其子孙、甚至如同刘禅这样的无能之辈也能左右朝政,最终导致国家分裂。封建论者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,因此劝诫大家(郭老)对秦始皇应少加指责,对于焚书坑儒之事也应理性讨论。这并非郭老个人的结论,秦始皇迫害知识分子(统一度量衡,亦需统一思想)时,秦灭六国之际也有众多儒生遭受牵连。
诗篇中所提到的“祖龙”,实则是指秦始皇,即便他已逝去,亦即秦始皇的离世。所谓“十批”,乃是指郭沫若所著的著作。当时,我提出了两个疑问;首先是“祖龙”的含义,主席解释道,它指的是秦始皇;其次是关于“历代都行秦王政”中的“政”字,是赢政的“政”还是政治的“政”(鉴于秦始皇名为赢政),主席明确指出,这里的“政”指的是政治的“政”,即依照秦始皇的治国策略。至于“孔学名高实枇杷”,意指孔夫子的学说虽然声名显赫,实则并无实效。而“熟读唐人封建论”,则是指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(子厚为其字),但不应将论述追溯到柳子厚之后,而应回归到周朝。至于“文王”,则是指周文王。

毛远新提及孔子的学说时表示,主席认为,孔子在其时代,其理论未能得到认可,因而四处游历,却屡遭排斥,原因何在?
战国时期,七雄争霸,唯独秦国禁止孔夫子之徒入内。自商鞅变法以来,其他诸侯国虽许孔子弟子(彼时孔子已逝)前往讲学,然而,那些曾信仰孔夫子的国家为何最终却纷纷衰亡?
唯有秦国,在秦始皇摒弃孔子学说的影响下得以实现统一,这不正应了那句话吗!自秦始皇离世后,农民起义频发,楚汉争霸,刘邦击败项羽,再次统一了国家。此后,历经汉、三国、魏晋,直至南北朝、元、明、清,历代的皇帝虽然口头上批评秦始皇,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纷纷效仿他的做法。这难道不是“说一套,做一套”的道理吗?
众口一词地指责秦始皇为暴君,然而在实际行动中,他们的手段并不比秦始皇温和。秦始皇曾坑杀四百余人,而后续的皇帝们又何尝不是如此?文字狱的残酷程度一浪高过一浪!大家纷纷效仿,因此历代君主都沿袭了秦王政的做法。实际上,那些表面上尊孔崇儒的名声,不过是虚有其表。
主席指出,孔子的诸多言论虽被誉为至理名言,如今看来亦不失其价值,然而,当置于现实社会的纷繁矛盾之中,孔子所倡导的理念似乎难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,它们似乎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因此,这些言论在现实中似乎成了空洞的言辞。都是主席的话。
领导人指出,历史上有许多农民发起反抗,而统治阶层内部也常常因权力争夺而更迭皇帝。每当这些反抗发生时,反抗者都会对孔子进行批判。这是因为孔子的学说中强调君臣之道,认为臣子不应反抗君主。若要推翻皇帝,就必须违背孔子的儒家思想,因此必须批判孔子,否则起兵的理由就失去了正当性。例如,刘邦就曾轻视儒生,甚至在见到儒生时会将帽子摘下撒尿,这在史书中有所记载。然而,到了汉武帝时期,儒学被独尊,这表明当掌握了统治权之后,统治者又会重新启用孔子的理论来治理国家。
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,这是一场在河南发生的军事政变,他成功推翻了皇帝,自己穿上皇袍登基为帝。这种行为与孔子的教诲相悖,显然是不相符的。然而,在他成为皇帝后,却又重新尊崇孔子,将孔子的思想请回朝廷。他在反叛时批判孔子,而在治理国家时又推崇孔子,表现出了这种矛盾的态度。至于成吉思汗,他是否研读过《论语》不得而知,但他的铁骑横扫欧亚,所向披靡,甚至有将所有农业区变为牧区和草地的野心。
然而,进入元朝时期,后继的皇帝亲赴山东祭祀孔子,对孔子的地位推崇备至,不仅头顶高帽,而且封号显赫。似乎元朝皇帝对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到了明朝,朱元璋起兵反抗时,他并未推崇孔子,这显然是认为造反无需理会孔子的教诲。他本人对孔子持有反感的立场。
朱元璋登基后,便计划前往曲阜进行孔庙祭祀。同样地,清朝时期,即便努尔哈赤的学识有限,满族入主中原后,实行了“剃发易服”政策,这与孔子的教义似乎相悖。然而,清朝皇帝继位后,却开始推崇孔子。至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,他起初批判孔子,若非如此,他可能不敢发动起义。但当他成为南京的天王后,却转而尊崇孔子。
毛远新表示,无论是国共两党的先驱孙中山,还是陈独秀、李大钊,他们都认为“五四”运动是从批判孔子开始的。是这样的吗?随后,蒋介石上台后转而推崇孔子,并举行了祭孔仪式。蒋介石还将孔氏后人接到台湾,他们至今仍居留在那里。
我国的史实不正是如此吗?每当民众奋起反抗,总会掀起一股批判孔子的风潮。用我们的话来说,当你是革命党派时,自然批孔;而一旦成为执政力量,为了巩固地位,又转而尊崇孔子。我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。这究竟是为何?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呢?
汉朝时期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主席曾指出,如今的孔夫子并非古时的孔丘,历代统治者依据自身需求,为他塑造形象。用鲁迅的话来说,所谓的孔孟之道,实则是由御用文人精心修饰过的孔夫子形象,他们以此思想体系束缚民众,成为思想专制的工具。回顾我国历史,是否确实如此呢?
毛远新提问道:“蒋介石真的深信孔子的教诲吗?共产党宁愿冤枉一千,也不愿放过一个,孔子又何时教导过他这一原则?孔子倡导的是和谐至上,那么主席当时推行那样的政策,又基于何种考量呢?”主席之所以提出批孔,其意在强调,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守自身的革命精神。
领导人指出,回顾历史,每当革命时期,往往都是从批判孔子开始,待到他掌权后,又会将他请回,目的何在?无非是将其作为维护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手段。因此,主席的论断何在?他明确指出,孔子,这位古代中国卓越的思想家与教育家,与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荀子等先贤同列,均应受到我们的尊敬与缅怀,更值得深入探究。因为这些先贤的思想,实际上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,其价值值得每一位国人予以崇高的敬意。
然而,孔子的这一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,提倡政治倒退,难以被认同。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批判孔子,鲁迅曾指出,我们批判的并非真正的孔子,而是经过历代粉饰后的形象。孔子也只是提到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”,但自南宋起,妇女缠足等行为对身体的损害,以及男尊女卑的现象,这些在孔子时代并未达到如此极端。尽管如此,这些现象的理论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想。
主席指出,我们共产党人自批判孔子始,然而,我们绝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辙,即批判之后又尊崇。若是我们为了巩固自身地位,将孔子的思想与民众的观念相融合,却陷入历史循环的陷阱,这便不可取。若共产党自身陷入无法掌控的局面或遭遇困境,转而将孔子请回,这预示着我们的衰败将至。
毛远新回忆道,主席曾言,我国并无一种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,这与西方大相径庭。主席以例佐证,他比喻说,耶稣与孔子相仿,在当年亦备受迫害,甚至被钉于十字架上。他们所创的学说,在当时均有其合理性,然而到了欧洲的中世纪,教会却沦为压迫和奴役民众的最恶劣工具。
主席指出,自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以来,资产阶段革命的发端便是针对教会,对神的批判,这与我国对孔子的批判颇有相似之处。然而,这里的教会并非质疑耶稣本人的教义,而是指要打破这一体系,资产阶级革命方能崛起。当时的教会实质上是宗教裁判所,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越法院。众多科学家因此遭受迫害,如哥白尼、伽利略等,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,否则将面临被处死的命运。
这难道能归咎于耶稣吗?显然不是耶稣的问题。然而,鉴于中国缺乏此类宗教,便以孔子的思想来治理国民。在中国,一切以实用为导向。生病了,想要孩子便祈求神灵,孩子一旦健康出生,便很快将此事淡忘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曾对宗教进行过批判和改革,经过改造,宗教得以适应资产阶级社会。因此,今天的宗教与中世纪的宗教有着显著差异。
毛远新说,主席深思良久,心中所想的是,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,那么我们就应当运用这一思想来启迪民众。孔夫子的言论虽言辞优美,每一句都堪称经典,难以指摘其错误,然而,它们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
延 伸 阅 读
王年一:“我是秦始皇,蒋是儒学之尊。”
批孔资料

作者:王年一
中国历史学家
曾获优秀教员称号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林彪坚定地秉持着“紧跟”毛泽东的宗旨。在处理中央传阅的文件时,他所遵循的原则是“主席划圈,我便划圈”,换言之,即“毛泽东若同意,我便赞同”。
大动乱的年代:
1949-1976:中国历史时期
凯歌行进的时期
曲折发展的岁月
林彪本人通常不亲自圈划文件,这一任务多由其秘书代为执行。在公开发言时,他运用精心构思的丰富“生动”词汇,对毛泽东进行了赞颂。每逢林彪登上天安门参加集会,他都会要求秘书严格掌控时间,确保其提前一两分钟抵达,于城墙下的电梯旁静候毛泽东的到来;而在天安门之上,他则始终紧随毛泽东的脚步。林彪素来不阅读《毛泽东语录》,亦不随身携带,而是规定秘书负责保管。每逢林彪出席群众集会,秘书便会将《毛泽东语录》交到他手中。在群众高呼口号之际,林彪会举起右手挥动《毛泽东语录》,一上一下地展示。集会结束后,《红宝书》便再次回到秘书手中。1966年,林彪向毛泽东提交的文件上,均以“请主席阅”、“送主席批示”等措辞;自1967年年初起,此类措辞均被统一替换为“呈”字。
“所有提及之处,一律划去!”
1967年3月20日,林彪于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。在讲话的尾声,他提及一个独立且零散的问题:“此外,我还要提及一个小问题。近期,我发现市面上出现了所谓的‘林彪同志语录’,这些语录是由学生所整理,其中一份来自一所中学,另一份则出自某个红卫兵组织,我们已收到两份。此外,总政治部曾整理过我的政治工作语录,我认为不宜继续这样做。若你们在今后看到此类语录,请代为收缴。我已经向总政表达过我的立场,这个决定是坚定不移的,请你们切勿再行整理。”
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,中共中央发布《林彪同志致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》。信中,林彪于1967年6月16日深夜表述道:“不宜高呼‘祝林副主席永葆健康’的口号。唯有凸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,方契合全国乃至全球革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客观现实。今后,在所有演出、会议、文件、报刊及各类宣传场合,均应凸显毛主席的形象,不宜与我一同提及。”翌年夏日,林彪外出途中,目睹街头上“纪念林副主席八·九讲话发表周年”等巨型标语,返家后即刻下令,要求立即将这些标语予以清除。
“郭老离柳宗元已远,不及先贤;自称共产党员,却崇拜孔子的先辈。”同年7月4日,毛泽东在与王洪文、张春桥的交谈中提到:“郭老不仅尊孔,更是反法。”
“请君少些对秦始皇的责骂,对于焚书坑儒之事亦需深思。尽管祖龙之魂已逝,秦朝的遗迹依然存在;孔子之名虽显赫,实则不过是空谈。秦朝的法律制度流传至今,而那些‘十批’的批评文章则显得不甚得体。熟读唐代人的《封建论》,切勿跟随柳宗元回归到文王时代。”
8月7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《孔子——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》。9月23日,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: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,我也是秦始皇,林彪骂我是秦始皇,中国历来分两派,一派讲秦始皇好,一派讲秦始皇坏。我赞成秦始皇,不赞成孔夫子。”
《林彪与儒家思想》(资料一)指出:“克己复礼”被视为孔子企图恢复奴隶制的反动宣言。林彪及叶群多次强调“克己复礼”,这一行为显然暴露了他们急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图,将资本主义复辟视为头等大事。若真是如此“暴露”了他们的野心,为何他们还会堂而皇之地将写有“克己复礼”的横幅悬挂?叶群难道不会这么做?实际上,“克己复礼”不过是旧瓶装新酒,含有“自我约束,遵守规矩”的含义。林彪和叶群将此挂在显眼处,实为“伪君子”。此外,将“批判林彪”与“批判孔子”混为一谈,存在诸多牵强之处。
秦始皇曾焚书坑儒。对此,我们的主席曾言:“秦始皇乃是一位崇尚现今而轻视往昔的专家,一位崇尚现今而轻视往昔的专家。”在我复述此言后,他紧接着反驳道:“秦始皇又能算得上什么?他不过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,也就是儒家学者。相较之下,我们在镇反运动中打击的,乃是几十万反革命势力。在我看来,四万六千名反革命知识分子,其数量已远超秦始皇。”
在与民主派人士的论战中,有人曾将我们比作秦始皇,然而这并不准确。实际上,我们的影响力已超越秦始皇百倍。若有人指责我们为独裁者,我们对此予以接受。”
6月14日,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“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”中,重点阐述了所谓的“儒法斗争史”,并呼吁撰写文章批判“现代儒学”。江青表示:“当前文章中鲜少提及现代儒学。”“难道我们如今已无儒学存在?并非如此,为何还要反孔二?现今是否仍有儒学?当然存在,而且影响颇大。蒋介石堪称其总代表。”
以儒法之争为界线进行筛选,凡历史的每一步前进,均被归结为法家的功绩;而历史的每一次倒退,则被归咎于儒家的过失。凡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人物,无一不被赋予法家的称号,而那些历史上的反面角色,则无一例外地被划归为儒家之列。
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,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进行了荒谬的解读:称法家思想为进步,而将儒家思想定性为反动;法家主张变革,儒家则倾向复古守旧;法家强调团结与统一,儒家却被视为制造分裂的源头;法家被颂扬为爱国和抗战的象征,而儒家则被指责为卖国投降的代表;法家似乎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,儒家则似乎总是逆流而行。该运动推崇封建统治的经纬与权谋,大肆宣扬所谓的“法、术、势”——即封建统治阶级的刑法、权术与权势。借评价秦始皇、曹操的历史角色之机,公然为他们残暴、凶狠、滥用暴力的行为辩护。
1974年4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《恃革命暴力者昌,恃反革命暴力者亡》一文,对秦始皇大加赞誉,称其“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实为佳举”。然而,该文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引发了破坏性的影响。
不仅摒弃了我国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,更对社会主义社会所确立的伦理道德规范造成了严重损害。对“师道尊严”的批判引发了师生关系的紧张。对“宽厚”、“忠恕”、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等传统“人性论”的质疑,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准则。
对“中庸之道”的批判和对“斗争哲学”的宣扬,更催生了一批人身上带有尖锐锋芒的极端好斗心态。在父子、母女、夫妻、兄弟、同志、朋友以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,原本和谐的社交关系遭受破坏,被誉为礼仪之邦的我国,其伦理道德水准亦随之大幅下滑,“文化大革命”在民众思想深处留下的创伤愈发深重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地区被迫推广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的口号。农民在耕作前必须面朝东方行礼,而工人在机床前亦需对领袖画像鞠躬致敬。此时,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之风盛行,成百、成千、上万乃至数十万的民众为一句“最新指示”的发布,彻夜狂欢,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某些省委书记在九大结束后,率领代表团返回省会,不仅带头跳起了“忠字舞”,更是从车站舞至省委机关。一位老工人因清理领袖塑像上的尘埃,竟被诬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遭受了长达数年的“专政”。原来,他的手触碰到了塑像的颈部,这一动作被认为带有“谋杀”的嫌疑。
五岁的孩童在嬉戏间,不慎将一枚纪念章套在了猫咪的颈间,母亲只得带着孩子一同承受那场“革命”的洗礼。一位印刷工不慎错排了一个铅字,一位贫农社员不慎念错了口号,一位机关干部则因疏忽将印有照片的废纸投入了废纸篓,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冠上了“阶级敌人”的罪名。“向右看齐”的指令曾被认为颇为不妥,有人甚至主张应更正为“向左看齐”;而交通信号中红灯要求车辆与行人暂停,也曾被指责不当,有人主张应以绿灯取而代之。
国内可靠的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